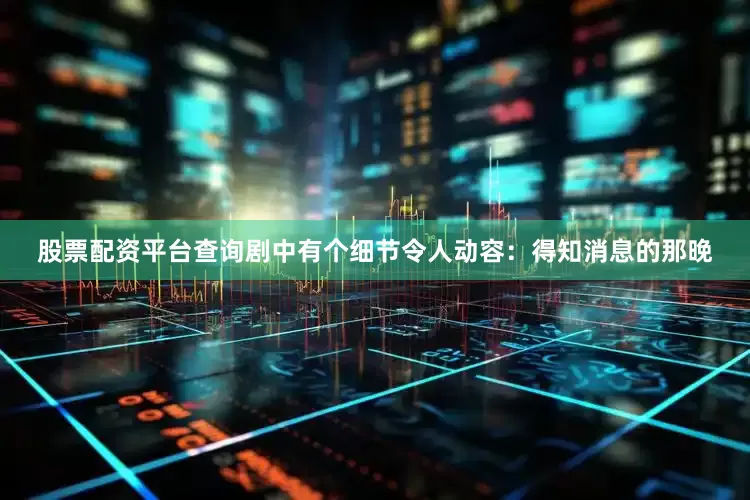
当抗联战士小驴子浑身湿透地从冰冷的江水中被救起时,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贴上 “叛逃者” 的标签。这个在野马滩长大、跟着父兄一起杀鬼子的少年,不过是想回家找失联的二哥,却要面对禁闭室的冰冷和战友的质疑。在《归队》这部聚焦抗联战士绝境归途的剧集中,小驴子的 “私自回国” 事件,撕开了战争宏大叙事下普通人最真实的情感褶皱 —— 所谓叛逃,不过是一个少年对故土最朴素的执念。
一个名字引发的恐慌
小驴子的归国之路,始于一个巧合的名字。苏联战友阿肖勒的牺牲,像一颗石子投进他早已紧绷的心湖。因为他的二哥二驴子,俄文名正是阿肖勒。
在此之前,二驴子奉命潜入长白山深处调查日军动向,约定三个月后归队,可大半年过去,音信全无。当小驴子在苏联营地听到 “阿肖勒牺牲” 的消息时,少年的心瞬间被揪紧。剧中有个细节令人动容:得知消息的那晚,小驴子抱着二哥留下的旧棉袄坐了整夜,棉袄上还留着长白山的松油味。这种对亲人的牵挂,让他无法再安心待在衣食无忧的苏联营地。
展开剩余71%导演臧溪川在采访中提到,《归队》要展现的是 “具体的人的故事”。小驴子不是天生的英雄,他会害怕、会牵挂家人,会因为一个名字的巧合而方寸大乱。这种不完美,恰恰让这个角色变得可信。就像老山东说的:“他还是个孩子,心里装着的先是家,再是国。”
安稳背后的精神困境
苏联营地的生活,对辗转于山林的抗联战士来说,无疑是天堂。这里有充足的粮食、崭新的枪支,不用再担心日军的搜山和刺骨的严寒。可小驴子却总觉得 “心里空落落的”。
剧中有段集体唱《松花江上》的戏码:当战友们为寻找小驴子遗失的枪集体下水时,福庆突然唱起 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,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。高云虎喊出的那句 “你们想家吗?想打鬼子吗?”,其实道出了所有战士的心声。对他们而言,苏联的安稳是 “寄人篱下的幸福”,而祖国的白山黑水,哪怕硝烟弥漫,才是真正的家。
小驴子在禁闭室里对老山东说的话,至今仍让人眼眶发热:“我不是逃兵,我是找二哥、打鬼子去。” 在这个少年的认知里,战士的价值不在安稳的营地,而在抗敌的战场。这种朴素的价值观,比任何宏大的口号都更有力量。编剧高满堂曾表示,创作《归队》时采访了多位抗联后人,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明白:“抗联战士不是神,他们的坚持往往源于最朴素的情感。”
不是叛逃,是归队的另一种形式
当小驴子被关禁闭时,老山东顶着 “连坐” 的压力,依然选择相信这个少年。因为他知道,小驴子的 “私自回国”,本质上是对 “归队” 精神的另一种诠释。
在《归队》中,“归队” 早已超越了军事指令的范畴,成为一种精神信仰。福庆曾说:“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八棵松,把我的名字刻上去,这样我就是死了也算归队。” 对小驴子而言,回到祖国的土地,找到二哥,继续杀鬼子,就是他心中 “归队” 的方式。
剧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:小驴子在江水中挣扎时,怀里紧紧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,上面用红笔圈着家乡野马滩的位置。这张地图,既是他回家的路,也是他抗敌的决心。当老山东最终撤销对小驴子的 “叛逃” 指控时,他说:“咱们抗联的根在祖国,只要还想着打鬼子,就不算真正走散。”
《归队》用小驴子的故事告诉我们,英雄从不是天生的。他们可能是会因为牵挂家人而 “犯错” 的少年,可能是会在安稳中怀念战场的普通人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人,用最朴素的信念,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,撑起了民族的希望。小驴子不是叛逃者,他只是一个想回家打鬼子的少年 —— 而这样的少年,才是抗联精神最真实的传承者。
发布于:安徽省倍顺网-线下配资官网-平台配资-十大股票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